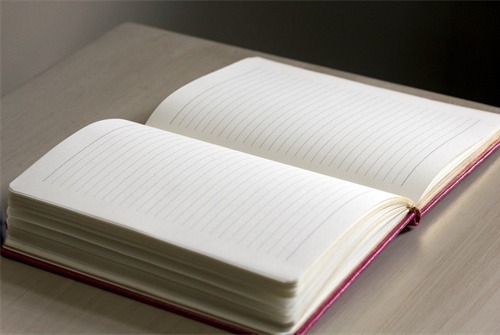一
我住在隔離病室的一床。其實我也不太清楚這是什么病,有點發燒有點胸悶,兼之我怕死怕的要命,就跑到醫院里來了。沒事,現在的人,哪個的靈魂或肉體不在病的路上。
隔離病室的人總是很安靜,像一朵朵蓬松松的蒲公英乖巧地倒著。冷冰冰的護士姐姐來的時候,懂事地張開嘴量體溫。過分的靜謐,和動輒大吼大叫的正常人差太多了,使得病房里有股清新而又古怪的汽油味,在消毒水的鎮壓下,在空虛憤懣簡直要燒起來的心也會化為這個味道。
我的爹媽最怕我有個頭痛腦熱,看見了這么個“燒”與“悶”的預警,快馬加鞭把我送到明晃晃的針頭下。也許他們堅信醫生是萬能的,也許是夫妻相看兩相厭,防止照顧女兒時當面吵起架來,一折中就奔這兒了。
不錯不錯,這年頭真當是普遍,分居是離婚中委婉又含蓄的表達,再飾以工作的借口,很好的讓一家子都心安理得。縱偶爾有個小病的突發情況,醫院也是很理想的避難所。把我安頓到這兒的頭天他倆碰了個頭,付完押金后各削給我個大蘋果,考慮到作嘔的胃酸,我很有骨氣的選擇了不吃。于是緊接著,兩人像商量好了似的,氣勢洶洶逼問我離了跟誰過。基于一個真理:小時候吵架孩子流流眼淚還是很值錢了,大了大了就賤賣了,我已經不再大吵大鬧。看著他們黑臉對望,恨不得用最陰險狠毒的話將對方剜得皮開肉綻,病房里熱鬧的像踩了地雷。一轉身兩人又笑得無比燦爛,等著從我嘴里摳出值得滿意的回答。
我被炸得支離破碎了。沉默地等了幾秒鐘,咣一聲,唔,終于安靜。
好快的變臉速度!我極其自豪而又萬份心酸。有一瞬間我心力交瘁很寬容的想算了算了世事本就如此艱難便放婚姻一條生路,早死早超生。立刻又暗罵自已好生沒毅力怎能背叛苦守多年的信仰。
二
不久我就莫名其妙接到了一個電話。微弱的快斷氣的鈴聲仍固執地打破了死一樣的寂靜。“你的的是什么病?”一個甜蜜蜜的聲音問。盡管我在爸媽面前軟弱得不行,可是對外交際方面還是像驢糞蛋一樣,表面光,優雅淑女的禮貌反問永遠是賣乖的好經驗。“請問您是哪位?”“哦,就是你隔壁了。”同一時間,我們目光相會,她慢
慢轉過眼珠子來,黑白隔得很勻稱。我才發現她的眼睛和我的好像,有月亮一樣柔軟的光暈。“好吧,我覺得不舒服而已——如果這也算是病的理由的話。”
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玩起了電話線,聲音更加輕渺。“好嬌氣啊,小姑娘一個,還怕受傷呢。”估量著相仿的年齡,我很不服氣地哼一聲,“你呢?不是一樣嗎?”“我可不是。我是很多年很多年前住進來的,那時我覺得病房好小,側側身就滾下床了。可是我知道,這地方是有限的,可以讓人清晰的感到存在,護士醫生們,就算是拿了錢在奔波,也是光明正大的行徑,混的熟了甚至會對病人掏真心。也許我得的病叫做‘厭世俗’,只要看到窗外無止盡的樓房,就像老天創造的病室,所有的人為了幾張床游走,不稱職的大夫往他們血管里注入壞東西,他們病著,卻自以為身強體壯,把一堆垃圾,比如車房名利當作保健品每天不斷藥。我看著隔離病室的人們來來去去,只有我一個留了下來,因為他們看不出來,在這小小的房間能隔離開多少瘋傻之人。”
我忽然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看著她就像覺悟先鋒一樣自豪的神情。“這里真是…安靜啊,有個說話的朋友最好了。”“朋友?”她咀嚼了一下,“怎樣就算朋友了呢?”質疑比恭維有力量得多,我想起來小學時候的天真之至,每天和所謂的好朋友勾肩搭背,最后詩情畫意地和她促膝談心,讓其深深領悟了少年的為難,家庭的不睦。于是我收獲頗豐,直到畢業我都在旁人的竊竊私語和同情又諷刺,溫柔得像刀一樣的眼神,溫暖的不能再做做的安慰里度過。
上了初中之后我正式定義其為背叛,立即明白了做人的艱難,倉頡造字時取了個怪名叫“秘密”,就注定要被朋友拿來暗地分享。我很有自知之明地明白自己沒有那么討人愛,就學會了三緘其口,這更與媽媽教我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不謀而合。
“心交朋友錢交狗。”這是我的經驗。她像將一切都了然于胸,遙遠的聲音從電話線那里運輸來,“你以為,她們交朋友都先按兵不動,然后拿把鋼尺量量你的成績夠不夠好,漂不漂亮,受不受歡迎,如果及格了就做到你的身邊,但是萬一出現一個分數更高的,她們就會趕緊一言不發撇清關系跑了。你呢?你認定了某某,也不是受了世風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