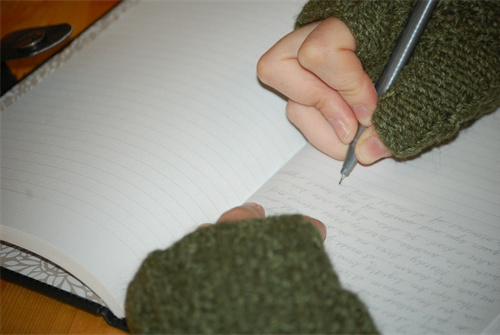這些人的一生幾乎沒有一天快樂,他們每天夜以繼日地工作都是彌補(bǔ)他們內(nèi)心的殘缺或是盡可能創(chuàng)造出他們認(rèn)為完美的藝術(shù)靈魂。
貝多芬是大家熟知的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他的一生寫出了無數(shù)的音樂巨作,但他內(nèi)心所承受的寂寞和悲傷更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從小父親給他的壓力,愛情的一次又一次失敗,然而這些令人意想不了的痛苦遠(yuǎn)遠(yuǎn)比不上耳聾帶給他的煩燥、抑郁,但也正是因?yàn)樗亩@,使他體會(huì)到了人生的昏暗以及內(nèi)心對(duì)外界聲音的強(qiáng)烈渴望,讓他寫成了更多令人震撼的鴻篇巨著。
米開朗其羅,這是一個(gè)極矛盾的悲劇人物,他有英雄化了的天才,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無與倫比,他以無窮的精力永遠(yuǎn)追求藝術(shù)的盡善盡美。但他的意志卻不是英雄式的,他精神軟弱無力,只能掙扎而沒有力量奮斗。他沒有一絲一毫的溫暖,只能用沒日沒夜的工作來填補(bǔ)自己空虛的心靈,以至于在他死前一周他依舊堅(jiān)持站著工作。
至于托爾斯泰,羅曼·羅蘭把他看作老師和世界的“精神權(quán)威”。盡管托爾斯泰有種種矛盾和弱點(diǎn),羅曼·羅蘭仍把他列為“英雄”,主要就是推崇托爾斯泰的博愛精神,他認(rèn)為托爾斯泰不是那種生在藝術(shù)與智慧的寶座上的大師和天才,相反—如他在信中自稱的那個(gè)在一切名稱中最美的一個(gè)—“我們的兄弟”。
在羅曼·羅蘭筆下,這三個(gè)英雄人物的一生都為藝術(shù)而存在,但同時(shí)又都擁有極悲痛的人生—他們一生中有著大大小小許多疾病,但都不肯去醫(yī)治;他們沒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生活、愛情,但令我更為嘆服和驚異的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死看作解脫、釋放、歸宿。甚至認(rèn)為這是應(yīng)該被祝福的。如果再聯(lián)系他們的一生,那么這令人驚異的思想就不再使人驚異了—
他們的生命是痛苦的,他們想要改變現(xiàn)狀,但事與愿違,他們想要?jiǎng)?chuàng)出靈魂的藝術(shù),卻又與他們所處的社會(huì)有所不融……
當(dāng)合上這書的時(shí)候,或許才會(huì)體會(huì)到什么是靈魂的藝術(shù),什么是心靈的煎熬,什么才是最具有真正意義的英雄。